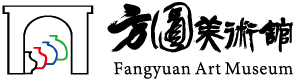全東明-陶藝創作Ⅰ
簡歷
89/08 「台東陽光、草原、風」展(聯展)/台東市公所
96/11 「磐陶到你家-周美智師生聯展」(聯展)/臺南縣立文化中心
97/12 國防部福利總處台北周年慶特展(聯展)/台北市國防部福利總處
100起/ 每年一次南投陶藝學會會員聯展及台灣陶藝學會會員聯展
101/10 台灣原住民文化當代陶藝創作展(個展)/台南市立新營文化中心
101/12 第一屆pulima藝術獎展覽(聯展)/松山文創園區
103/11 第二屆Pulima藝術獎展覽(聯展)/台北當代藝術館MOCA Taipei
104/09 陶藝接力特展「布農板曆陶藝展」(聯展)/南投縣文化園區南投陶展示館
104/09 在府城耕作‧Maomah(聯展)/臺南市原住民文化會館(札哈木會館)
106/09 鶯原際會—臺灣原住民陶藝展(聯展)/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107/05 原來在這裡:臺灣原住民族陶藝展(聯展)/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108/04 磐陶N次方 周美智師生聯合陶藝展(聯展)/台南市立新營文化中心
110/09 臺南人文藝術風情(一) /方圓美術館
(得獎)
91/原舞祭/第一屆中華汽車原住民工藝獎佳作
94/陶醉的布農/高雄縣鳳邑美術展/原住民藝術特別獎優選
95/守護/高雄縣鳳邑美術展/原住民藝術特別獎優選
96/曙光/高雄縣鳳邑美術展/原住民藝術特別獎優選
97/酒、戒/高雄縣鳳邑美術展/原住民藝術特別獎優選
98/獵人勇士/高雄縣鳳邑美術展/原住民藝術特別獎優選
99/得獎作品「曙光」及「酒、戒」獲高雄縣文化局典藏,目前收藏於高雄市立美術館
99/那瑪夏的春天/高雄縣鳳邑美展/原住民藝術特別獎優選
101/Tama的眼睛/第一屆pulima藝術獎入選
103/黑洞/第二屆pulima藝術獎入選
當初筆者受命去訪談原住民陶藝家全東明先生,腦中浮現的刻板印象是原住民and陶藝家,沒想到他竟擁有多元的身分,超乎我的想像,他是原住民、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家屬、台灣女婿、軍人、詩人、福利站經理、陶藝家和民宿主人,這麼多重的身份讓他的人生特別精彩。
他的名字
全東明先生是布農族人,於民國四十一年(1952年)八月出生在南投縣信義鄉。他總共有三個名字,Dian(迪洋)、洪東明和全東明。「Dian」是他原住民母語的名字,在布農族的文化裡,都是沿襲祖先留下來的名字,長子(女)承襲祖父(母)的名字,其餘子女按照排行承襲伯伯、叔叔、姑姑的名字,很少另外創立新名字。他之所以會叫Dian,就是因為他排行第二且有一個伯父叫Dian,現在他有二個孫子,第一個孫子沿襲祖父的名字叫Pagi(巴給),第二個孫子則沿襲他的名字Dian,他說他們都是這樣子傳承名字的。這樣一來,一個家族可能好幾個人都叫Dian,不知道當他們家族聚會時,忽然傳來「Dian,外面有朋友找你。」會有幾個Dian同時回應?其實不用擔心,布農族人只有對平輩會直接叫名字,對輩份高者會在前面加Tama(爸爸的布農族語),Tina(媽媽的布農族語),即「Tama Dian」和「Tina Dian」;對輩份低者會在名字後面加Van(孫子),即「Dian Van」。
「洪東明」是全東明先生原本漢語的姓名,他的生父是洪成先生,他當然跟著姓「洪」了。到了國中二年級,因離婚後的媽媽和全天祥先生重組家庭,他和哥哥被繼父收養,所以跟著繼父的姓,從原本的「洪東明」變為「全東明」。他的繼父和媽媽知道他不想改姓,所以也沒有告知戶籍上已改姓的事,不管是之後國中畢業後去讀軍校或後來在軍中服務,他都使用「洪東明」這個名字十多年(居然都沒事?!),直到要去辦理結婚登記,他才發現他早已姓「全」,而他的夫人王秋香女士也方知道原來她口中一直以來稱呼的「洪大哥」,其實應該是「全東明」全大哥,而他趁這次的機會把他所有的證件都改為「全東明」。
童年生活
之一:
前文有提到全東明先生是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家屬。他的爸爸洪成先生是原住民的菁英分子,曾擔任警察,卻因大甲案入獄,整整有十年之久,當時的他還在媽媽的肚子裡。他的媽媽洪阿嬌女士也是很優秀的人,在部落的小學畢業後,被選派去參加護理和接生等的相關訓練,受訓完後回到信義鄉擔任助產士的工作。在那個醫療尚未普及的年代,信義鄉境內規模比較大的部落設有衛生所,裡面編制一位醫生和一位助產士;規模比較小的部落則設置衛生室,只由助產士一人打理有關的醫療事務。當時產婦若要生小孩的話,都是請助產士到家裡來接生,洪阿嬌女士曾在地利村衛生室擔任助產士八年,這段期間該村的新生兒都是她接生的。
丈夫無端被捲入政治案件而入獄,洪阿嬌女士很堅強,同時扮演嚴父和慈母的角色,一肩扛起照顧三個孩子的責任,她生的二個兒子和領養來作伴的一位姪女。她管教子女很嚴格,全東明先生說:「媽媽故意把錢放在看得到的地方,哥哥會拿去買東西,媽媽知道以後,把哥哥吊起來打,打完後自己躲在廁所裡哭。」打在兒身痛在娘心。
之二:
許多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家屬在當時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如常常得擔心警察來調查戶口、受到鄰居或朋友的歧視或蓄意的疏離、求學或求職路步步坎坷難行等等,相對來說,全東明先生算是較幸運的,他受到的負面影響較小。其原因如下:
第一,他的媽媽很有擔當,是家庭的重要支柱,因為擔任公職,每個月有固定的薪水,政府也會配給生活必需品如米和油等,經濟狀況不錯,忙不過來時還有請人幫忙打理家務兼陪伴孩子,所以他的童年生活被照顧得還算好,以致讓他就沒有想太多或要埋怨甚麼的。他的同鄉曾任原住民委員會主任委員尤哈尼先生回憶起小學那段日子,他說那時他好忌妒全東明先生,「因為原住民幾乎沒有收入,很難得買東買西的,大多數同學都打赤腳上學,他卻天天穿制服、穿皮鞋或球鞋…。」針對這點,他倒是全然不知他和同學有什麼不一樣,他說自小他就沒有比較心,一直到現在做陶藝也是一樣,不會去比較誰的陶藝做得比他好,「不和人比較」是他的特點之一。
第二,當時大家對白色恐怖大多是噤若寒蟬,不敢提也不敢問,以免自己也惹禍上身。再者,爸爸被捕事件是發生在東埔部落,事件發生四年(1956年)後媽媽洪阿嬌女士被調離該地,之後輾轉搬過幾次家,那些地方的人對這事件較陌生,所以他們一家人並沒有受到特別的關注。而且,他和媽媽住在行政區的宿舍裡,較少在部落活動,又布農族採散居,部落地方大,族人分散住,即使有事情發生也比較不會到處傳。他很少聽到部落的人提到他爸爸的事,也不曾被嘲笑是個沒爸爸的孩子,一路走過來有媽媽的保護和照顧,「爸爸不在」這件事對他生活層面的影響甚小。直到最近幾年原住民轉型正義受到重視,他有機會翻閱相關資料才知道真相,怨嗎?恨嗎?語氣平淡的說:「不。」
之三:
因為媽媽的工作地點會調動的關係,全東明先生前後搬過幾次家,他提到以前原住民居住的地方分二部分,一個是部落,即一般原住民居住的地方;另一個是行政區,通常警察、老師、公職人員等人和其眷屬住在這裡。幼兒時期他和外祖母住在望鄉的舅舅家,他的媽媽則在東埔村衛生室擔任護士,民國四十五年(1956年)被調動到地利村衛生室擔任助產士,他在地利國小讀到三年級,後又搬到和社,進入同富國小一直讀到小學畢業,接著到信義初中就讀。因為住過不同的地方,跟著媽媽到不同的部落走動,讓他有機會接觸到不同的布農族文化與語言,布農族有五種語言,聲調不大一樣,他都聽得懂,原來搬家多也有好處!
民國五十一年(1962年)五月,全東明先生就讀同富國小四年級,家裡有了變化,被關了整整十年的爸爸獲釋回家了,應該事件高興的事?洪成先生雖然重獲自由,卻鬱鬱寡歡,應該是這十年的牢獄之災帶給他太多的傷痛,二年(1964年)後他選擇與妻子離婚。全東明先生就讀初中二年級時,媽媽再婚,他的繼父全天祥先生也是菁英份子,自二十多歲開始從政,不是當南投縣議員,就是當信義鄉鄉長,反正只要任期滿了就轉換跑道當另一種身份。
讀軍校與從軍
之一:
全東明先生的另一個特點是很喜歡讀書,很用功讀書,完全不需要媽媽督促。在初中時期他的學業成績表現優良,每學期都是班上的前幾名,照常理應該繼續升學讀普通高中,怎麼會去讀軍校?真是跌破大家的眼鏡。他整理了五個他想讀軍校的理由:第一,他很喜歡大自然,喜歡海闊天空,想遨遊世界,如果去讀海軍相關學校,就可達成這個夢想。第二,小時候他的腸子有毛病,送到信義鄉的小診所就醫,醫師束手無策,表示無法開刀,要媽媽把他帶回家等死。然而他的外祖母不死心,每天用小米熬湯汁給他喝,他竟然奇蹟式地活過來,從那時候開始,他的身體狀況雖然一直很OK,但不夠強壯,他認為軍校的磨練對身體健康可能有幫助,就立志讀軍校了。第三,前文提到成長過程中,「爸爸不在」對他生活層面的影響不大,然而在他內心的隱微處、在他的潛意識裡總是少了些甚麼,是一種說不出的感覺,他想用讀軍校、當軍人來表達自我獨立與存在感。第四,他家附近有一位國小老師,曾當過軍人,對他很好,經常對他提起部隊的事,講的多半是好的事,讓他嚮往軍旅生活。第五,也是最重要的理由,當時的教育強調反攻復國,崇拜強人,他想讓自己成為一個強大的人。綜合以上,他堅決讀軍校,但學業成績表現很好,家人當然希望他讀高中進大學,畢竟那是一般人所謂的成功之路。為了勸阻他不去讀軍校,媽媽還特地請牧師為他禱告,可是他的心意實在很堅決,發動絕食抗議,繼父和媽媽只好妥協,要讀軍校可以,要他去讀較能學到一技之長的空軍,他想做海軍去遨遊世界的夢想就在這次的協商中沒了。
俗話說:「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自古以來中國的封建思想是重文輕武,讓很多爸爸媽媽都不願送自己的孩子去讀軍校、當軍人。其實人各有志,找到適合自己的舞台發揮,活出自己的生命價值,才是最重要的。軍校所栽培出來的也是人才濟濟,全東明先生提到他空軍機械學校士官班的同學有一百多位,後來有人轉行當醫生、中醫師、畫家、音樂家、企業家、或公務員等等,也都相當傑出。而未來的戰爭,不是靠兵多也不是靠武器多,主要是打科技戰,利用高智能的武器方能致勝,因此更需要優秀的人,需要好男好女來從軍。
之二:
全東明先生十六歲(1968年)進入位在岡山的空軍機械學校(現今空軍航空技術學院)士官班就讀,從小喜歡讀書的他,一如往常很認真讀書,不但自己認真讀,也會規勸同學要努力讀書,現在開同學會,這段往事還常常被大家提起。他從小就是一個認真的人,不需要被督促,當學生時認真讀書,直到後來工作,當職業軍人,他也不斷進修和自我學習,從維修飛機,轉換跑道到當採購官、當監察官、當福利站經理、製作文化陶…,跨多種不同的領域,都能做得很好,實在是因為他凡事認真,對應做的事都下足功夫的關係。
軍校士官班畢業後,全東明先生被分發到岡山的中華民國空軍官校負責維修飛機,那時在他的心裡面,仍存有那個「海闊天空」的夢想,至少讓自己離開台灣本島吧,二年後他試圖請調到金門服務,但天不從人願,金門沒有職缺,不過澎湖倒是有缺哦,「無魚,蝦嘛好」,他就這麼去到了澎湖,在那裡的飛航管制中心服役二年,不在他的人生規劃,卻誤打誤撞,是他一生中的鑽石黃金時期。
澎湖,好地方!「外婆的澎湖灣」這首歌許多人耳熟能詳,「晚風輕拂澎湖灣 白浪逐沙灘 沒有椰林綴斜陽 只是一片海藍藍…」全東明先生每天看看大海、看看天空,算是「類海闊天空」?!喜歡閱讀、追求自我成長的他在這段時期讀了許多書,澎湖縣圖書館是他常待的地方,他大量閱讀心理學和哲學的書籍,「看這些書不是因為自己的心中有困頓,而是想從書中知道自己的想法與別人是否有差異、有不一樣」,他發現自己有些想法和一些作者有雷同之處;如果遇到想法不一致,他會認真去思考其差異性。他說今天台灣有許多的原住民信仰基督教,他也一樣,從小信仰基督教,但他尊重任何一個宗教,他說:「現在的我,宗教觀比較成熟,所有的宗教都要被尊重,只要你相信祂,祂就會給你力量。」
之三:
不想當一輩子的士官,為了更上一層樓,全東明先生考入母校空軍機械學校的軍官班,重新當學生,喜歡讀書的他當然還是很用功,以第一名畢業,那一年還當選「南投縣模範青年」,報紙有特別報導他的故事哦。第一名當然可以優先選擇服役地點,有獨到想法的他認為人還是要做自己喜歡、自己想做的事才會快樂,他想過如果到台北服役,以他隨和的個性自然也會融入當地的生活,無適應上的困難;若到台南,民風比較保守,選擇對象比較能符合家人的期待,果然是適婚年齡會有的思維,還真的來對了,他就是在台南這裡找到他的真命天女。
就這樣全東明先生來到位於台南機場的台南空軍聯隊工作,因為在學期間曾鑽研如何處理未爆彈以及如何防爆,所以有段時期他也擔任防爆處理小組的一員。印象最深刻的,民國六十六年(1977年)七月七日「反共義士」范園焱先生駕著編號3171的殲六偵察機來台灣投奔自由,這件事在當時是相當轟動的新聞。為了深入了解中共的武器,他受命拆解該飛機上的機械和彈頭,以便進一步做質與量的分析,被指派這個任務他感到很光榮。
之四:
全東明先生不是一個打混過日子的人,他喜歡閱讀、勇於突破以及追求自我成長,在擔任軍官的這一段職業生涯,工作性質開始轉為行政事務的處理,與他原來維修飛機是截然不同的領域。沒關係,勤能補拙,他積極參加有關的研習與短期訓練班,有新工作新任務來,他不害怕也不推拒,就去學習,學管理、學採購等,熟知的領域越來越多,多元的歷練交出漂亮的人生成績單。他擔任過採購官,為了做好採購工作,他到國防財經學校讀採購班,學會了要採購甚麼物品,如何有效地運用這些物品,如何簽契約等等。要向國外採購物品,要具備外語能力,行嗎?因為在原鄉長大,他會說五種布農族語和日語,國語和台語嘛也通,至於英語,沒問題的,初中時期他拿整本英文字典來背,會說好幾種語言,真的很強!
結婚後一、二年全東明先生當少校,他負責的工作又改變了,擔任監察官,工作內容主要是監督察查工程、軍紀、預算和採購等等,他發現自己的個性非常適合這樣的工作,他是一個心中有愛的人,會幫助被老兵欺負的新兵;他是一個有正義感的人,對於官官相護和貪瀆等等都會依法處理,更重要的是妥善處理,是「空軍的包青天」。這樣剛正不阿,會不會得罪人?他認為「人要行得正,充滿正能量,想到整個部隊是一個生命共同體,就沒有甚麼好怕的。」當然這樣的人難免受到「有些人」的不歡迎,促成他在民國八十四年(1995年)元旦從空軍機械學校中校軍官退役,四十三歲退休算是早了點,不過有才的人不怕沒處去,退休後他無縫接軌,立馬到福利總處台南站當監察員,是大家搶破頭想要的一個職缺哦!聽說坐那個位置的人通常需要有很好的背景,而且通常是上校。為了瞭解自己是否適合這個工作,他還特地穿著中校的制服實地勘查,真是明目張膽…,福利站的人員見狀,猜想他只是中校而已,而且這個位置居然懸缺了四個月就等他來接掌,可見他的背景很強,心裡偷偷地怕了一下下,哪知他是一點背景都沒有,能當上福利站的經理,只能說「就實力好唄」。
陶藝之路
之一:
如果單看全東明先生的學歷和工作經歷,他與藝術創作是沾不上邊的,事實上他從讀軍校開始就已踏入這個領域。他從小生活在大自然中,喜歡大自然,會想把大自然剎那間的變幻之美記錄下來變成永恆,進入軍校後開始摸相機、學攝影,最後沉迷於此,把閒暇時的興趣幾乎當專業來經營。對喜歡的事、想做的事會很投入很鑽研是他的第三個特點。
要拍出美美的相片,當然要有好的相機,全東明先生的第一台相機是Konica的雙眼相機,價錢不低,大哥出手毫不手軟。美還要更美,相機和相關配備越買越多,越買越貴。再者,要拍美景就得到處趴趴走,上山下海,玉山、小琉球…台灣很多地方都有他的足跡。而為了追求自己想要的效果,他甚至連照片都自己沖洗。還有,為了精進攝影技術,除了和同好互相交流,他也買了許多相關的書籍和期刊雜誌。這麼投入攝影是很花錢的,他表示在結婚前所賺的錢幾乎都砸在這裡,是「月光族」。
能拍出好的攝影作品,全東明先生表示要感謝二個人,第一個是一位大專兵,入伍前他就是當攝影記者的,攝影技術一級棒,很感恩他毫不藏私地傳授攝影技術。另一位則是軍隊中的攝影室班長。為了記錄軍隊中發生的大小事,台灣的軍隊裡都設有攝影室,所拍攝的照片也由該單位負責沖洗,以免重要資料外流。攝影室班長知道他喜歡攝影,不但交流攝影技術,也毫不藏私地傳授照片沖洗技術,有高手相助讓全東明先生的學習攝影之路更佳順暢。
之二:
「藝術是相通的」,投身於攝影對全東明先生往後的陶藝創作之路有很大的影響,而究竟是什麼因緣讓他人生的下半生走上陶藝創作之路?這得先從飲茶開始說起。他剛結婚時沒有分配到眷舍,也沒有錢購買房子,只好選擇在台南亞洲航空公司的附近租屋,當時他的妻子王秋香女士在台南縣政府服務,每天得台南和新營兩地通車,暈車很厲害,尤其懷孕時更加辛苦,體貼的他決定搬到台南市鹽水區的岳父家住,換成他每天通車。哇!是寵妻一族。
岳父住的地方是一個三合院,除了全東明先生的岳父母外,還有其他的長輩同住,岳父和長輩都喜歡泡茶喝。他的妻子笑笑地說:「我們二人在交往期間,他經常會去鹽水找我爸爸喝茶聊天,即使我不在家。」不簡單,很懂得和長輩拉攏感情、建立關係。接著她說起這段喝茶的經過:「我的伯父喜歡在大廳泡老人茶,有時看到他,就會邀他一起喝茶,他不好意思違逆老人家,長輩請喝茶就禮貌性地把茶喝完,我伯父看他喝完,以為他喜歡喝,就會再添、一直添,他心裡納悶,好奇怪,這茶又濃又苦,怎麼會有人喜歡喝?於是他就開始研究茶,在當時我們沒有汽車,他自己還曾經騎著摩托車從鹽水到鹿谷去買茶葉,一次就買兩三斤,一斤一兩千塊,一個月的薪水也才一萬多。」有點敗家,而且真的很想買喲!來回好幾百公里的路,不辭辛勞也要騎機車去買到手,全大哥當軍人,有練過的,沒在怕!民國七十三年(1984年)他開始喝茶,也愛上喝茶,現在的他很喜歡品茶,遇有好茶就會買回家。
王秋香女士接著說:「剛開始家裡沒有泡茶專用的茶壺和茶杯,他就拿普通的杯子來泡,並做成紀錄(筆者的OS:哇!好有科學研究的精神)。就這樣喝了一陣子,升級了,開始買茶壺、買聞香杯,他買的第一把壺是紫砂壺,因為上面有小瑕疵,只花了八百元就買到了。好還要更好,全東明先生的茶具越買越貴,「後來有人推薦周美智老師製的壺,她的壺造型很美,壺壁很薄。」王秋香女士說,「當時是民國七十多年,有小孩要養、有房貸要付,我只好和他約好,用年終獎金去買,一年只買一、兩個壺。」現在的他雖然自己會做茶壺,但看到別人做的茶壺或茶杯,只要喜歡的,他都忍不住要買來收藏。
「太太不給我買,看看總可以吧!」全東明先生常去周美智老師家賞壺,他也很喜歡廖俊嘉和王明發二位老師的作品,經常和製壺的老師們交流不同的壺所泡出來的口感,透過交流老師也從中受益,所以老師們常會把新燒的壺讓他鑑賞。
之三:
人生的禍福有時很難只憑一時來論斷。民國七十六年(1987年)全東明先生被調到台中清水服務,長達二年。當時他和妻女早已在鹽水落地生根,無奈軍令難違,他只好單身赴任,周末才回家。被迫與家人分居,心裡實在很不舒服,平日的晚上該如何打發時間?果真是愛茶、愛壺的男人不會變壞,他到處找茶和茶壺,找到了茶葉達人陳先生的工作室,那裡是台中地區很有才的藝術家很愛聚集的地方,在那裡也可以看到大陸走私進來的茶葉、茶壺和古玩,在那海峽兩岸不通的年代,能看到這些東西算是開了眼界。每天下班後,他就到陳先生那裡去串門子,也因此認識一些影響他走上陶藝之路的製壺和書畫的老師,有陶藝家李幸龍先生和陳文濱先生、書法家李亂先生等,大家互相交流學習,兩年下來,讓他不知不覺中成為一個頂流的品茗與鑑賞專家。現在再回頭看「被調到清水服務」這件事,應該是件好事吧?!
或許是藝術細胞蠢動了,全東明先生要求周美智老師幫他客製化他心中想要的陶藝品,具原住民風的,老師認為「形象可以代為做出來,但內在的精神是無法幫他做得來的。」既然自己有鑑賞力又有想法,老師鼓勵他自己動手做,並送他陶土和手動的轆轤。這些東西來到了家裡被閒置了好一陣子,直到他調到新營的福利站當經理,那裡規模小,工作較輕鬆,他總算有時間、有心情DIY做陶了,這一年是民國八十八年(1999年)。
全東明先生為了泡出好喝的茶開始做茶壺和茶杯,從此踏上陶藝創作之路,這過程只拜過林春輝先生為師學習手捏陶三個月,其餘都是靠自我摸索,只要遇到障礙,就會動腦筋去思考、多方嘗試。陶藝製作的方法有好幾種,他個人偏愛做泥條、用手去捏陶,他表示有些人做陶藝品時,會使用工具來幫助作品快速完成,但他很少利用工具,他喜歡用手慢慢地做,這樣做出來的東西會有手感,把自己的感情放入陶土裡,「做陶是要用生命去和它互通,不是說你想完成一件作品,就拿陶土當做材料來捏塑;你要把陶土當做是自己的生命,把生命投注在上面,它自然會讓你感覺有生命力,這樣做出來的作品更有味道、更有力度。」細細想慢慢做,做工精緻,真是不簡單!他表示他都是抱持這樣的心態做陶,所以他的作品都是有故事的、能感動人的。
創作理念
有人用口說歷史,有人用筆寫歷史,全東明先生用陶記錄歷史。他開始製作文化陶,把他所思、所見、所聞用陶記錄下來,他的紀錄不具批判性,即使面對曾經的不公平對待與折磨,只是誠實的呈現過往歷史,這是筆者很敬佩的地方。他說:「我創作的靈感來自我血液裏的文化,還有就是我對大自然的喜愛,而且因為我小時候看到的一些不平等的現象,讓我產生很強烈的一種使命感,所以我就把使命感用在這裡,寫下歷史,寫下文化。」他說他的創作構想是將台灣原住民的傳統文化與當代發展史相結合,並以陶作表達創作理念。他的創作理念主要有三:
第一,板曆是在南投縣布農族所在地發現的,它是唯一有文字意義的圖騰,記錄了一年時序重要誌事,對沒有文字紀錄的台灣原住民發展史而言更顯珍貴,其重要性足與八部合音相提並論。
第二,洞察台灣原住民的近代史,有原鄉的天災人禍,有城市謀生的不易,有人口減少,有土地、文化和語言流失,雖然近年來政府有重視這些議題並尋求改善,但原住民依舊是弱勢的族群。以少了一隻眼睛,但永遠保持微笑的抽象臉譜,來表達原住民是天性樂觀、懂得分享的民族,期盼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的所有人們,共享多元文化瑰麗的饗宴。
第三,推廣陶藝作品,喚起祖靈記憶,傳承傳統文化,延續生命智慧,讓全世界都看到台灣文化之美。
創作特色
全東明先生的創作主要目的是記錄歷史和傳承傳統文化,其作品特色有:第一、他的作品是有故事的,他是抱持著記錄歷史與文化的心態來創作,所以觀賞者一定要了解作品背後的故事,了解後等同於閱讀了台灣發生過的一小段歷史文化。第二、他的作品數不多,投入陶藝創作約二十年,他重質不重量的,實際作品件數不多,每件作品都是把他的經歷或看法在腦海裡千迴百轉後,才動手表現出來,作品醞釀過程有時要花上一、二年,難怪件件是精品,而且是值得細心品味的精品。第三、他的作品都是僅做一件,不做第二件,他作品的尺寸也算大,筆者問他作品是否失敗過?他說,首先要有「做陶藝很簡單」的信念,在創作的過程,若發生問題就去思考該如何做,不急,慢慢做,這樣做出來的作品即使尺寸很大都不曾在捏塑或燒製過程崩壞,實在有夠厲害!
全東明先生以原住民傳統文化為精髓,佐以當今時代的重大變異為元素,立志創造出有深度、廣度及高度之大器作品,同時將陶藝的實用性結合原住民文化藝術元素,呈現多樣及實用的當代藝術之美。他期許台灣當代原住民的文化與藝術之美能夠走入國際,讓世人瞭解、學習台灣原住民達觀知命的生活態度,也藉此喚醒原住民對自身的榮耀進而永續經營。
非賣品?
作品賣不賣?喜歡的作品送給朋友會不會捨不得?全東明先生的作品除了文化陶,有些是生活器物如茶壺、茶杯和茶倉,除了樣貌有意思外,功能性強,尤其茶倉經過柴燒後,裡面含有遠紅外線,用來存放茶葉,味道會轉化,泡出來的茶好喝不會苦澀。朋友喜歡他的作品想買回家,他卻只做不賣。他說:「做陶的時候要很專注、要有衝動、要有熱情,以及滿滿的自信,要憑自己的審美觀與感覺,想著要做出什麼樣的作品,才可以把它做得很完整。如果心裡想著要做什麼樣的東西才會賣錢,通常這件作品一定不會好看。」不過最近他的想法改變了,他的妻子跟他說,作品要和人交流,這是一種愛的流動,東西交流出去後會接觸更多的人,遇到許多喜歡它的人。
作品賣錢與否從來不是全東明先生的考量,他表示他可以把作品送給朋友,不過他最大的想望,就是未來把作品都捐給原住民博物館(位在澄清湖附近,目前仍興建中),他說:「我用作品來記錄文化和歷史,它不是做來賣的或是展覽的,是要把它留下來,留給後代子孫,讓他們知道這塊土地曾經發生過什麼……。不管如何,最後的最後,我的作品都要捐出去。」實在好樣地。他是陶藝家也是歷史紀錄者,透過作品忠實地記錄歷史,他沒有用尖銳的角度或偏激的語彙來批判,即使面對原住民被平地人欺負,即使面對白色恐怖的受難,他還是微笑、還是愛與分享,這是很令人感動的地方。
作品介紹 1
在全東明先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些屬於原住民的元素,如微笑臉譜、板曆裡的象形文字、百步蛇圖騰、花圈、琉璃珠等等,這些元素用來代表該件作品要表達的內容與原住民有關。以下針對他的作品做綜合的介紹。
(一)原住民文化的守護者
有人說:「血緣是騙不了人的。」十六歲時全東明先生到平地讀書,之後就業、建立家庭,一直到現在六十多歲了,算算他真正住在原鄉的時間不長,但重要的是他身上留著原住民的血液,心裡住著原住民的靈魂,對自己的血統有強烈的認同感,即使現在每天說漢語、穿西服,他還是道道地地的布農族人。
全東明先生小時候住在信義鄉,是原住民聚居的地方,話說當年,許多往事歷歷在目,令他印象最深刻的事有二,首先,在他五歲以前,外祖母帶著他到望鄉部落和舅舅一家人同住。一般原住民的住屋是石板屋,舅舅家是二房一廳一廚一儲的四方格局,房子的周圍則用木板做圍籬。他和外祖母共同使用一個房間,另一房間則是舅舅一家六口一起睡覺的地方。儲藏室裡存放著小米和其他糧食,小米是他們的主食,每到用餐的時間,廚房中間的地上排放三塊石頭,上面放置一個大的鍋子,裡面滿滿的小米飯,很香,大家蹲在鍋子的四周,用一個木製的小瓢挖著小米飯吃,這是原住民傳統的飲食文化,迄今是他最深刻的印象之一。
民國四十五年(1956年)外祖母病逝,全東明先生只好到地利村與媽媽一起生活,住在行政區裡,當時他的媽媽在地利村衛生室擔任助產士。他說他曾在那裏看到一群布農族的青壯年人手持長獵槍,集結在地利派出所,接受槍枝管制檢驗,他們的服裝吸引他的注意,一身的裝扮都是獸皮製的,這是布農族的祖先留下來最傳統的衣服,是他最深刻的印象之二。
除了親身體驗的,還有耳聞的。全東明先生說他住在行政區時,在派出所服務的一位耆老金先生非常有智慧,告訴他許多有關原住民各部落的祖靈傳說和歷史故事,他很喜歡聽,細心聆聽並牢牢記在心裡,這些口述歷史在適當的時機都釋放出來,化為他創作的題材,使得他的作品具故事性與生命力。
更重要的,「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其實祖先留下來的靈魂或文化一直都在,都在我們的內心裡。全東明先生說,他曾造訪台灣各地的原住民部落,與在地的長輩或小孩聊天,他可以感受到過去的文化存在這些談話中;他曾到台東拜訪從事雕刻或陶藝的原住民藝術家,他可以從他們的作品看到過去的文化,他強調只要透過內心熱衷地去感受,就一定能感受到這些文化的存在。
而他自己也一樣,一脈相承的文化就在他的內心裡,也出現在他的作品裡。全東明先提到他的「獵人勇士」,作品內容主要是說原住民在山上蓋房子時,一個年輕人會爬到很高很高的樹上去,尤其是最硬的櫸木,向著山裡揮揮手,請大自然把最好的空氣、最好吃的食物、最美好的運氣全部來到家裡。這一段內容是沒有文字紀錄、文獻看不到的,可是當他在做這個作品時,他就是有很強烈的感受,他的祖先在幾百年或幾千年以前是這樣做的。他曾跟別人說起這一段故事,有人跟他說這是他裡面住的老靈魂出來告訴他以前是這樣子的;他相信當人在創作一個作品時,住在身體裡面的老靈魂自然會跑出來把以前發生過的故事呈現,「沒有人告訴你怎麼一回事,心裡面自然會和它相通」,他的一些作品都是這樣創作出來的。
因為認同自己的血統,熱愛自己的文化,全東明先生立志要守護原住民的文化,讓它能持續傳承下去。文化傳承的方式有很多種,一般人常用的是書寫的方式,為何選擇用陶藝來記錄原住民歷史與文化呢?其實全東明先生也曾是文藝青年,年輕的時候喜歡閱讀,也常提筆作詩作詞,所以他曾起心動念想要書寫歷史,不過「成功不必在我」,他發現已經有人將原住民歷史與文化做了很周詳的書寫紀錄,那人就是他的族人--布農族文學創作家霍斯陸曼•伐伐(漢名王新民),他生前致力於透過學術研究與文藝創作來推廣與保留布農族文化,留下的著作有:《玉山的生命精靈》、《中央山脈的守護者─布農族》、《那年我們祭拜祖靈》、《黥面》、《玉山魂》,以及一些原住民的相關研究。對文化傳承同樣有強烈使命感的全東明先生,在拜讀這些作品後,決定改用陶藝創作來記錄歷史,讓原住民文化的傳承更多元化。
作品介紹 2
(二)心中有愛
全東明先生的作品裡,如「微笑臉譜」、「Tama的眼睛」(註:布農族語「爸爸」是Tama)、「Tina的眼睛」(註:布農族語「媽媽」是Tina)等可以看到少了一隻眼睛,但永遠保持微笑的抽象臉譜,這是他自創的圖騰,他表示這個微笑臉譜是他這輩子永遠的logo,它創作的靈感其實是深埋在他的心裡很久很久的一些故事。
在全東明先生很小的時候,看到一些平地商人到山上買油桐子、篦麻子或獸皮等等,他們會故意把秤頭拉到最後面,用這個方法巧妙騙取原住民的錢;把假酒拿到部落來賣,導致原住民喝了以後死亡;或者用很便宜的錢來購買山上的土地。平地人對原住民的種種不好的對待,他看在眼裡,並深刻地烙印在腦海裡,所以他創作一個「微笑臉譜」,一個空的眼睛和微笑的嘴巴,空的眼睛代表原住民被人欺負,就好像一個眼睛被挖掉了;雖然被欺負,還是要保持微笑,微笑的嘴巴代表台灣這塊土地上有多元的文化與種族,希望大家能互相包容,共享這美麗的台灣。真得好好誇一下,原住民的天性樂觀、懂得分享,對欺負他們的人仍然可以正面對待,這是多麼大度的胸懷。
原住民的天性是樂觀知命、愛好和平與分享。全東明先生說原住民的心思單純,對家人和朋友都很好,部落裡的雜貨店都是平地人開的,若是原住民開的店,自己人來買不付錢也沒關係,很難長期經營。
「有東西要與人分享」,布農族有狩獵祭,打獵回來就把獵獲物和族人一起分享,即使只分到一小塊也好。王秋香女士提到台灣人結婚是發喜餅,布農族人則是分豬肉,只要部落裡有人結婚就發豬肉給全部落的人,一次得殺十幾隻豬,分發前先擺放在部落裡的土地上(好壯觀的場面!),剩下的內臟就用很大的鍋煮來吃,配著小米酒,聽起來很豪氣。提起原住民結婚,場面最盛大的是排灣族,娶排灣族女孩要送很多禮物,整個迎親典禮持續進行幾天,大家吃吃喝喝不只一餐,很熱鬧但荷包傷很大,至少得花上百萬元,不過,沒在怕,就是愛分享。
關於「微笑臉譜」、「Tama的眼睛」、「Tina的眼睛」,作品裡說的是原住民被欺負的故事,他曾經糾結,要講比較好聽的場面話,編造美麗的故事,還是誠實地做歷史的陳述、記錄歷史?當然要誠實地陳述事實,筆者只比創作者小五歲,筆者也曾耳聞那些事情,是到今日不曾忘記的歷史啊。
作品介紹 3
(三)布農族的驕傲--板曆
在全東明先生的作品裡可以看到一些類似象形文字的符號,這些符號來自於布農族的板曆,板曆的發現翻新了台灣的歷史,是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
誰是台灣最早的居民?目前台灣島上以漢人為優勢族群,其實最早來到此落腳的是布農族與泰雅族,估計有五千至一萬年之久,可惜這段期間一直缺乏文字紀錄,只好稱之為「史前時代」。直到昭和十二年(1937年)考古學者在南投縣信義鄉進行田野調查時,發現地利村的卡尼多社(Qanitoan)頭目馬古德凡的家中有一塊長一百二十公分、寬十二公分的檜木板,上面有類似象形文字的圖形,因為是記載在檜木板上的行事曆,稱其為「板曆」,功能等同於漢人的農民曆;因為是記載全年應行之歲時祭儀及生活禮俗,也稱祭事曆(Islulusan)。學者認為這些圖形具有文字的功能,有其特殊的意義,布農族因此被視為台灣原住民中唯一擁有自己文字的族群。
在臺灣的原住民中,布農族人的農事祭儀特別繁複,是傳統祭儀最多的一族,為何會如此呢?布農族人長居高山,以農耕及狩獵為主,靠天吃飯,若能風調雨順,日子自然好過。古代布農族人採大陰曆法,依據月亮的圓缺,把一年分成十二個月,以結繩記事將重大的事件記錄下來,後來發展出「板曆」的象形文字,做為祭司(archpriest)施行祭祀儀式(ceremony)與指導族人從事農作的依據或備忘錄,是布農族祖先的智慧結晶,是很珍貴的文化資產哦!
布農族的八個傳統祭祀儀式有:
1)開墾祭:十一月到十二月尋找新耕地、開始農耕的祭典。
2)小米播種祭:二月告知祖靈即將播種之事,並祝禱小米豐收。
3)播種完成祭:三月告知祖靈播種完成,並祈求小米豐收。
4)除草祭:四月初開始除草,祈求穀物成長茂盛的祭典。
5)狩獵祭:四月底農閒季節獵取動物以充實食物,並取動物皮毛來做衣服和帽子。
6)打耳祭:五月初布農族最隆重、最盛大的祭典,具有團結精神的教育意義,對外來說,象徵著射獵敵首;對內來說,則象徵團結友愛。
7)收穫祭:六月開始收割農作物的祭典。
8)進倉祭:八月將小米存入米倉,祝禱祖靈保護小米不腐壞。
作品介紹 4
(四)百步蛇圖騰
一般人對百步蛇的印象是不好的,它有毒,會咬死人,看到它就驚慌失措,想辦法溜之大吉。然而在全東明先生的作品裡出現有百步蛇的圖騰,為什麼選擇這一圖騰來創作?他曾多方研究台灣原住民的圖騰,認為其中最能代表台灣原住民的圖騰就是百步蛇,不管過去或現在,它被使用得相當多,也曾被人格化或神格化。再者,百步蛇是布農族的好朋友哦,布農族人服飾上的圖騰與色彩都源自於它,所以當他的作品裡出現百步蛇圖騰即代表這作品要表達的內容與布農族有關。
百步蛇是布農族的好朋友,百步蛇的布農族語是「朋友」的意思,他們是怎麼結緣的?在布農族裡有一段這樣的傳說,相傳很久以前有一對布農族的夫妻,妻子想幫丈夫做一件漂亮的衣服,左思右想卻想不出要織什麼樣的花紋。有一天妻子在路上遇到百步蛇,看到了百步蛇的幼蛇,覺得它身上的花紋實在太漂亮了,便向百步蛇媽媽借小百步蛇一個禮拜,做為編織衣服的參考圖案,百步蛇媽媽勉強答應。布農族媽媽就把小百步蛇帶回家,回家後依照圖案很快的編織出美麗的衣服來,其他的村人看了很喜歡,也都跑來借用小百步蛇,借來借去,小百步蛇不幸身亡。
一個禮拜後,百步蛇媽媽依約前來帶回小百步蛇,布農族的妻子根本還不出來,只好以尚未完成衣服為理由,再借一個禮拜。之後百步蛇媽媽每週都來,她都以各種理由(小百步蛇失蹤了…)推拖,一個禮拜拖過一個禮拜,最後百步蛇媽媽生氣了,認為布農族人不守信用,帶著所有的百步蛇攻擊村子裡的人,而布農族人也不甘示弱見蛇就打;好幾百年間,雙方死傷慘重,為了平息戰火協議停戰,百步蛇同意讓身上漂亮的花紋做為布農族人織衣的參考,而布農族人則答應尊重百步蛇,不再屠殺它們,並以嚴肅且尊敬的態度對待百步蛇如朋友一般。
作品介紹 5
(五)白色恐怖
全東明的爸爸洪成先生在民國四十一年(1952年)五月因為大甲案被捕入獄,而他在同年的八月出生,民國五十一年(1962年)五月爸爸獲釋回到家中,爸爸在他的童年是缺席的,缺席了十年。對「爸爸不在」這件事,從小他不清楚爸爸為何被關,也沒問過媽媽,他坦言潛意識裡或許自己把這件事空白了,可是其實對自己的心理層面還是有些許負面的影響。透過轉型正義,打開潘朵拉的盒子,他接受了這個事實,並希望未來政府為這三位白色恐怖受難的布農族人在東埔立一個紀念碑,讓世人知道這一段歷史。
前年(2019年)負責原住民白色恐怖受難者口述歷史及影像紀錄的工作人員到全東明先生經營的布農民宿工坊去拜訪三次,他們也一起去信義鄉踏查當年的一些足跡,並與另一位受難者伍保忠先生的兒子伍金山先生見面。去年(2020年)他開始思考如何把這三位受難者的故事、把這段歷史記錄下來。在今年(2021年)四月初完成陶作,總計有四件作品,這些作品今年九月在台南市將軍區的方圓美術館做第一次的發表。觀看這四件作品,心平氣和,可敬的是,看不到怨或恨。只想留下紀錄,就這樣而已,他說:「這是歷史的包袱,是已經過去的事,今後我也不想讓自己的家人因這件事產生仇恨,影響未來發展。」這是一個悲傷的故事,筆者後續會針對這段歷史做更詳細的介紹,敬請期待。
結語
全東明先生有一股強烈的使命感,以陶藝創作來記錄近代的原住民歷史,他矢志在推動保存原住民傳統文化的道路上勇往直前。他希望在往後的歲月,找回原住民的熱情和純真,希望現今居住在台灣的各個不同種族,不管是漢人、客家人、原住民、新住民、外國人等等,都能快樂在一起,沒有歧視,沒有傷痛,只有愛與包容。